8月13日是“国际左撇子日”。你知道亚里士多德、达·芬奇、拿破仑、莫扎特、尼采、图灵、居里夫人、奥巴马、比尔·盖茨这些超级名人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一个隐秘的答案是:他们都是左撇子。据统计,全世界约12%的人是左撇子,约87%的人是右撇子,另有约1%的人可以左右开弓。不过,中国左撇子的比例只有1%左右(后天矫正的比例很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少数群体,左撇子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无论是被刻画为原罪者,还是被贬低为劣等种族或先天缺陷者,抑或被捧为天才或创造力的象征,其实都是戴着刻有时代印记的有色眼镜观察和审视的结果。探究左撇子的有趣历史,其实就是体认和反思人类偏见的历史。有时候,所谓历史,就是以一种偏见代替另一种偏见的漫长过程。

魔鬼与原罪
左撇子最初的不利处境与强大的宗教偏见密不可分。在大多数古文明中,右手优势既是生理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以西方文明的元典——《圣经》为例,《旧约·创世纪》记载耶和华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并让这对最初的男女生活在伊甸园中。众所周知,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不小心摘下了致人堕落的苹果。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摘下那个象征欲望的禁果,用的正是左手。从那一刻起,左手开始背上了本不该属于它的污名。15世纪尼德兰绘画大师雨果·凡·德·古斯在其名作《原罪》(1480)中,为我们完美呈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在此,善恶之树将画面分割为两个对立的世界,夏娃深入左边——即魔鬼的一边,进入了不属于她的区域。于是,原罪——左撇子之罪,标志着灾祸/左手(sinistre)进入了世界的精神领域。
在《新约全书》中,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文。在著名的《山上宝训》中,基督向他的门徒和追随他的人群传授他的教义。在那里,耶稣用六点指出先知的律法,人们不仅仅应该严格遵守这些律法,而且应该加以改善,使之臻于完善。其中,耶稣指出奸淫是罪恶,并且动了淫念与奸淫无异。他要求人们做到正直和遵守戒律,接着他说: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这条格言就记录在当时通行的象征体系中:人的命运取决于正确或错误地使用右手。后来,罗马天主教教父、著名《圣经》研究权威圣哲罗姆(约347-420)在解释上述经文时,其观点是明确的:
右手……象征意志和感觉的最初活动,它能使我们实现我们在头脑中构思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应该让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迅速变质。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右手遇到困难,那么我们的左手更是无能为力。如果灵魂放任自己,那么身体就更倾向于堕落。
其实,不只是基督教,在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众多宗教中都有“左卑右尊”的规定。比如,在众多宗教混杂的印度,吃饭等日常活动只能用右手,左手一般是用来上厕所或洗澡的“不洁之手”,因为左边是“恶魔”的方向。对此,我们可以从“右”和“左”的词源找到清晰的印证。拉丁语的dextra既表示“右手”,也以转义的方式表示“帮助”“友谊”“礼物”,这自然而然地赋予了右手以一系列具有正面价值的含义。在英语中,right是个显而易见的褒义词,作为形容词,它意为“正直的”,有时指“公正的”“合乎道德的”“正确的”“适宜的”;作为副词,意为“笔直地”“完整地”;作为名词,意为“善”“真”“正义”“秩序”。正好相反,“左手”始终与罪恶、厄运、不诚实和轻率等相伴随。英语中的left一词最早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单词lyft,意为“软弱、折断”;其他的欧洲语言中,“左”几乎无一例外地充满贬义色彩:意大利语mancino意为“欺骗”,德语linkisch意为“尴尬”;西班牙语zurdo带有“恶意”的意思。
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早期文献中,作家们总是将左手和某种充满罪恶的魔鬼形象连在一起。比如,公元二世纪的著名历史作家苏维托尼乌斯生动刻画了古罗马皇帝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B.C42-A.D37)令人厌恶的形象。除了书写其可憎的品行,苏氏还把这个残暴的皇帝描绘为“皮肤白皙,头发长的十分靠后,乃至覆盖后颈,脸上布满了小麻子。”此外,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着重强调了提比略是个左撇子:
他的左手比另一只手更灵巧、更有力;其筋骨十分有力,他能用手指贯穿一个刚刚摘下来的完整苹果,他用手指弹一下,就能使孩子或少年的头骨受伤。
在此,堕落的品行、丑陋的外貌、超自然的能力和恐怖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使提比略成为一个反常的和残酷的人物。尤为可怕的是,其灵巧的左手奇特异常,能实施违背常理的残忍举动,从而使这个魔鬼的形象臻于完善。
默许与宽容
和人们普遍对黑暗中世纪(Dark Age)的固有负面印象不同,中世纪对左撇子这一特殊群体表现出来的宽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治安和司法档案中,在伦理学、医学或神学论文中,在中世纪众多世俗和宗教制度留给我们的各类文献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左撇子受到有组织的社会迫害,受到追捕或某种形式的惩罚,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左撇子因其生理特征而受到有针对性的攻击。更准确地说,尽管左撇子的社会声誉一向不好,但他们在那个宗教裁判所暴虐横行的黑暗年代得到了相当的宽容。

《贝叶挂毯》
创作于11世纪的著名的《贝叶挂毯》(也称为《巴约挂毯》)向世人表明,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尤其在造船厂的工人中间可以看到左撇子,他们是这幅被誉为“西方《清明上河图》”的巨型画作的一部分。此外,巴黎的圣热内维埃夫图书馆保存了一部分类编号为775的手稿,亦即1471年在意大利誊写的《罗马史》(Historia romana)手稿。这是一部很普通的拉丁文著作,四开本,共485页。然而,它与其他类似的几百部手稿有一个惊人的区别,那就是在最后一页赫然出现的一段手稿誊写者的文字:
弗朗西斯科·桑托里尼,里米尼的议事司铎,用左手书写本书。
在此,桑托里尼大声宣布,这部书写完美的作品是他用左手写就的。这个左撇子带着自己的骄傲,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左手能与世间最灵巧的右手相媲美,而这段不寻常的文字作为出版物的一部分被默许和宽容,无疑是令人动容的。几十年之后,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师拉斐洛·达·蒙特鲁波在其回忆录中以更为直截了当的表述,流露出与桑托里尼十分接近的骄傲之情:
我想补充说,我是天生的左撇子,我的左手比我的右手更灵巧,我总是用左手写字。
当然,这种默许和宽容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中世纪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写字。换言之,某种社会性的书写规范并没有建立起来。例如,13世纪出版的一本关于书写规范的著作《书写规则》中,我们没有看到禁止用左手书写的规定;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用右手书写的建议。14世纪中叶,学者于格·斯佩茨哈德在其撰写的《书写规范》中建议用鸟的右翼羽毛而非左翼进行书写(根据当时流行的象征体系),但他没有明确规定应该用右手还是左手书写。显然,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并不重要。
几乎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餐饮礼仪上。如果我们查阅关于中世纪礼节的书籍,我们不难发现在用餐时使用哪一只手几乎没有明确的规定。要知道,当时礼节制度的规定十分详细而严苛,比如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不要吐痰,不要用餐巾擤鼻涕等。然而,在15世纪出版的著作《餐桌上的举止》中,对用餐时使用哪一只手的问题却保持沉默。换言之,人们不认为在用餐的时候必须用右手。其实,其中的理由也很简单:在那个餐叉还没有出现的时代(要等到17世纪,西方人才开始使用餐叉),人们直接用手吃饭。在他人的注视下,“用两只手轮流把肉塞进嘴里,同时用左右手吃饭”,没有人认为是粗野的。13世纪德意志抒情诗人汤豪泽在一首题为《宫廷礼节》的诗中虽然批评“同时用两只手吃饭的习惯”,却又明确地写道:
始终应该用远离邻座用餐者的手吃饭。如果你的邻座用餐者坐在你右边,那么你就应该用左手吃饭!
然而,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礼节运动和识字运动的兴起,各类社会行为的规范更加全面地建立起来,那个对左撇子默许和宽容的时代结束了。
双重压迫
在中世纪文化中,右手便利可能是一种生理规范,在象征意义上,它可能也是一种道德规范。但无论如何,右手便利从来都不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强制性规范。然而,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而来的识字运动和礼节运动,标志着中世纪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变。16世纪上半叶,骑士贵族制度走向没落,王室专制主义兴起,权力逐渐集中在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和在其周围的领导集团——宫廷阶层。对于这个阶层来说,礼节、礼仪、礼貌和其他表现方式是依附和尊重君主的标志。从此以后,宫廷生活的准则成为广义的“文雅举止”的典范,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1466-1536)是这套观念的最初倡导者。1530年,他出版的《论儿童的品行教育》影响巨大,不仅是当时的绝对畅销书,并成为现代礼仪手册的原型。其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在端菜和倒酒的时候,不应该使用左手。

伊拉斯谟
礼节概念和礼节所规定的社交准则的建立,为左撇子的自在生活敲响了丧钟。从此,左撇子受到了来自古代负面传统和新晋礼节规范的双重压迫。让我们来到17世纪80年代西班牙查理二世的宫廷,欧仁妮·马蒂内斯·巴列霍是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中的一个小女孩,在其周围是美丽的夫人和英俊的先生。除了人人都叫她“女怪物”,她与《梅吕斯纳故事》中的神话人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的欧仁妮获得这个绰号的原因是极其肥胖、四肢畸形。她被带至宫廷仅仅是为了满足那些伪善之士的病态好奇心,画家胡安·卡雷诺·德·米兰达多次对她进行了描绘。这些画作中有裸体的,也有穿衣服的,但有一个凸显的共同点:每次绘画的时候,卡雷诺都让小女孩用左手紧紧握住一样东西。正如它所暗示的,这个被强化的细节是为了增强小模特的生理特异性。根据古代的传统,这是魔鬼的特征。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强大的礼节规范开始进入社会的最底层,因为教会学校致力于向社会的最底层灌输基督教美德。从此以后,有了一种体面的用餐方式和一种不体面的用餐方式,使用左手用餐显然属于后者。1683年,受圣奥古斯丁著作启发的皮埃尔·勒佩蒂抨击性小册子证明了这一点:
你不是每天都责备左撇子和用左手吃饭的人吗?如果你相信在餐桌上用左手吃饭的人是不体面的,那么上帝何以不认为你用左手做应该用右手做的事,或用右手做应该用左手做的事是不体面的?
在法国,拉萨勒(1651-1719)是这种社会行为规范化的主使者之一。在1703年出版的《社交礼节和基督教礼仪准则》中罗列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过分讲究细节的程度远甚于其他同类书籍。这本以儿童为主要对象的书不给予儿童一点行动自由,却在之后的将近两个世纪中重印了近两百次,足以表明该书在西方风俗习惯史中的重要性。关于用餐时使用右手和左手的规定,在伊拉斯谟及其继承者的著作中只有几条,而在拉萨勒的著作中则多达几十条,并且这条严苛的清规戒律不仅适用于就餐的人,也适用于服侍的人。即便是对于自己七岁的儿子,拉萨勒也毫不留情:“我命令我的儿子严格地遵守神甫先生的教导,从此以后放弃使用左手,否则就不能得到我的右手的祝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右手的统治地位全面确立,这种境况将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左手革命
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三百年间,右手对左手的胜利所向披靡。无数的左撇子被强行矫正,苦不堪言。尽管从托马斯·布朗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多位有识之士为左手发声,但无奈势单力薄,难以形成气候。直到20世纪初,更多的人意识到强制性的右手教育可能对青少年产生危害。1914年,儿童研究专家们聚集在费城的东北学校,讨论“应该对左撇子儿童采取何种态度”。在讨论会上,他们宣布偏侧性是一种先天的现象,而非后天习得。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左撇子在使用右手时,能像使用左手那样表现出同样的灵巧。”不惜一切代价矫正左撇子的天性,可能使他们产生“严重的神经障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姗姗来迟的左手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大大加速了。1914-1918年间,数以百万计的战士在战争中失去手或手臂,其中无数失去右手的伤员必须学会使用左手,才能重新适应生活,政府和医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人怀疑这项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就这样,那些在过去一两千年里被传统观念否定的做法——诸如用左手写字,用左手使用工具,用左手吃饭,用左手在胸前划十字等等,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公民美德的标志,以及世界和平的象征。随之而来的是大众舆论的普遍觉醒,报刊大量刊登引发轰动的文章:《要尊重左撇子!》《对左撇子犯下的罪行》《不要束缚左撇子!》。作为全球首个把这些新口号付诸实践的国家,澳大利亚取消了学校里禁止使用左手的规定。效果是惊人的:其左撇子的比例从19世纪末的2%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的13%。
这场声势浩大的左手革命在20世纪下半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即越来越多的人将左撇子和天才联系在一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左撇子是“数学能力早熟”的一个预测因子,即左撇子预示着有超强的数学能力。该项研究发现,在有数学天赋的学生中,左撇子所占比例远远大于普通人群。其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表明偏侧性作为脑半球之间连通性的指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认知。也就是说,偏侧性只是大脑功能的一个间接表现。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解释人们的右手偏好,无论我们将其视为天才的标志,还是认知障碍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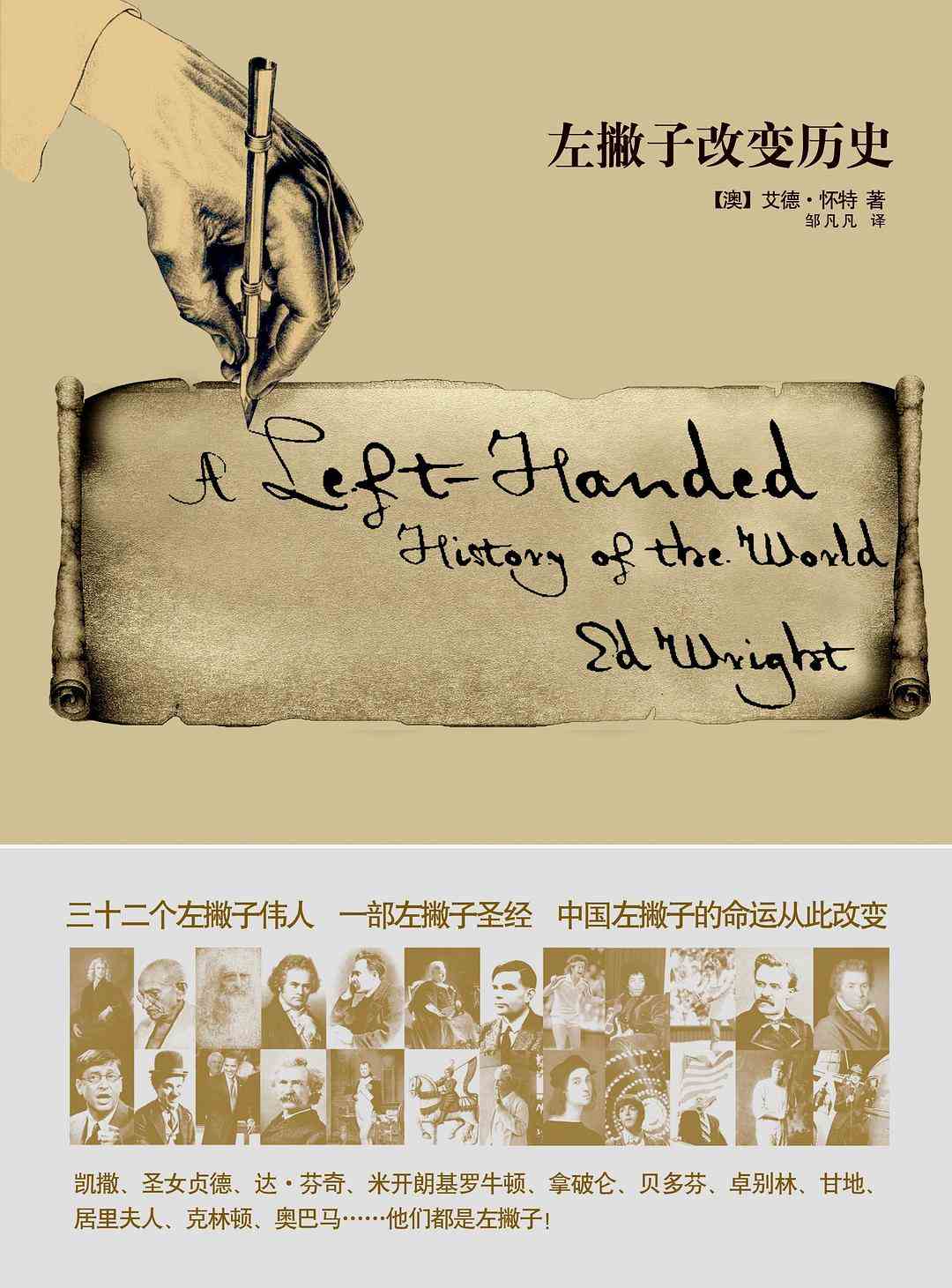
《左撇子改变历史》
然而,就像所有被压迫太久而得到平反的事物所可能产生的附加效应,总有一波又一波的媒体不厌其烦地列举人类历史上各个领域的左撇子天才,不断地将这群在历史上被污名化的小众群体推上神坛。一方面,许多媒体宣扬的天才并非左撇子,只是广为流传的谣言。另一方面,“达·芬奇综合征”在公众接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公众的印象中,达·芬奇不仅是天才的典范,也是左撇子的领军人物。这两个鲜明特征,即卓越的智慧和根深蒂固的左手便利,在同一个人身上形成和谐的共处,显然会使公众自然而然地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这种简单的心理暗示,传说就足以形成并永远地流传下去。
如今,当人们列举优秀的左撇子时表现出极大狂热,其实是缺乏科学精神的矫枉过正。当人们把天才的帽子戴在左撇子头上时,只是在无意识地恢复正统观念的右手便利者持有的排斥左手的古老偏见,尤其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几乎所有的设计都对左撇子“不友好”。更确切地说,人们只是用一种偏见代替了另一种偏见。说到底,左撇子不需要引起人们的羡慕,正如他们不应该受到蔑视。
